“下野”之后,我在无锡中语的江湖上,几乎是销声匿迹的。
当然,这是“双向脱钩”,他们不跟我玩儿,我也不跟他们玩儿。这倒不是说我们互生了嫌隙,而是体制内要讲圈子,我若不知进退,不肯退圈,还要时不时刷存在感,肯定让他们为难,我自己呢也不舒服。
所以,就这样渐渐地淡出,其实挺好。
当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秘书处王老师联系我,说第七届名师工作室学术年会在无锡举行,请我上一节课并做主旨报告的时候,我略略怔了一怔,才答应下来。之所以略略“怔一怔”,乃是不想在这个地界,以这样的方式抛头露面,以免不必要的误会。
但我随后又想,自我07年到江阴,18年来,无锡教科院组织的大市教研活动,我正儿八经也就只上过一次公开课,那是2012年,在侨谊中学上了一节市级公开课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没有在市级教研活动中粉过墨登过场——好嘛,趁此机会,就半推半就地上一节课试试。让无锡的老师,看看我这13年里有没有进步,也是挺好的。
前一天晚上,与几个语文朋友聚餐,饭后,我破例没有提议打几圈掼蛋,因为我要回来把课再捋一捋。隔天上午,吃过早饭,我就到了无锡,虽然我的课安排在下午3点。就在家门口的活动,为什么赶这么早去?因为当天狂风大作,我怕路上有突发状况,万一迟到了,让近千名与会老师等我,那罪过可就大了去了。
越是家门口的课,越是马虎不得。
我选的课题,是八年级下《石壕吏》,这篇课文的教读,应该是我第三次上公开课。第一次是在江阴初级中学,新课试上,我喊了中心组成员帮我一起磨课;第二次是在隔壁张家港,曹特的工作室活动,我应邀执教示范课。
同一篇课文,每次上,都会有新的感受,以及新的收获。
第一次教读这篇课文,读到“泣”,讨论“可能是谁在哭”时,有个男生举手,说“隔壁有人在哭”——这个答案在预设里是没有的,但这个孩子的答案真是绝妙啊,我大大表扬了他,并且把他的发现做在了我再教的预设里。
第二次教读这篇课文,孩子们对于老妪“请从吏夜归”的动机有不同的意见,有人说是老妇为国赴难,是牺牲精神;有人说老妇心里肯定是不想去服役的,她这是被逼无奈之举。这个“请”字的品读本就在我的预设里,但学生的分歧却是出乎我的预料,于是我就果断摁下后续活动的暂停键,把这个课堂“意外”解决了——因此最后一个环节:在原文某处加一个感叹词“唉”,读出诗人内心情感的味道——这个活动原计划要请七位同学来分享学习成果,结果只来得及喊了五位。当然,听课老师没发现我的“小动作”,评课时,曹特还特别夸奖这最后一个环节做得好。
第三次教读这篇课文,就今天。上课班级是无锡女中的学生,全都是女生,她们有点拘谨和腼腆,不怎么乐于举手,课堂的推进有时候还有点艰难,但她们也有特别靓的表现。其中让我最为欣赏的,是在讨论“可能是谁在哭”的环节,先是有个女生说是“小孩在哭”,另外一个女生反驳,说“小孩哭是嚎啕大哭,不会压低了声音哭”,先前的女生又反对了别人的反对,说“家里穷,孩子饿得没有力气大哭,只能'泣'了”——全场老师自发地鼓掌,我以为这是这节课最大的亮点。
在家门口上课,我其实也是有压力的。万一上砸了,那可就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啦。好在,听课老师们比较宽容,他们给了我热情的掌声,这应当是认同和鼓励了。
我想,老师们如此认同我的这节课,也许并不是这节课真有多么精彩,而是: 这是一节真实的课。对,真实!真实的学情,真实的课堂生成,真实的语文的方式教读语文,不灌概念,不玩噱头,不凑课改热词,在朴素的听说读写活动中教语文。
下课后,从无锡回江阴的车子上,我翻看“我们的语文”教研群里的留言,以及老师们的线上看课时弹幕的截图,我才知道,除了现场听课的近千名老师,还有线上观课的1.9万人,尤其令我感动的,听课者中,居然还有其他学科的很多老师,他们居然也纷纷留言表扬我。
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吧,所有学科公开课中,语文课的风险是最大的。它的风险就在于,其他学科的老师都喜欢听语文课,也都能看得懂语文课。不然呢,你让语文老师去听一节英语课试试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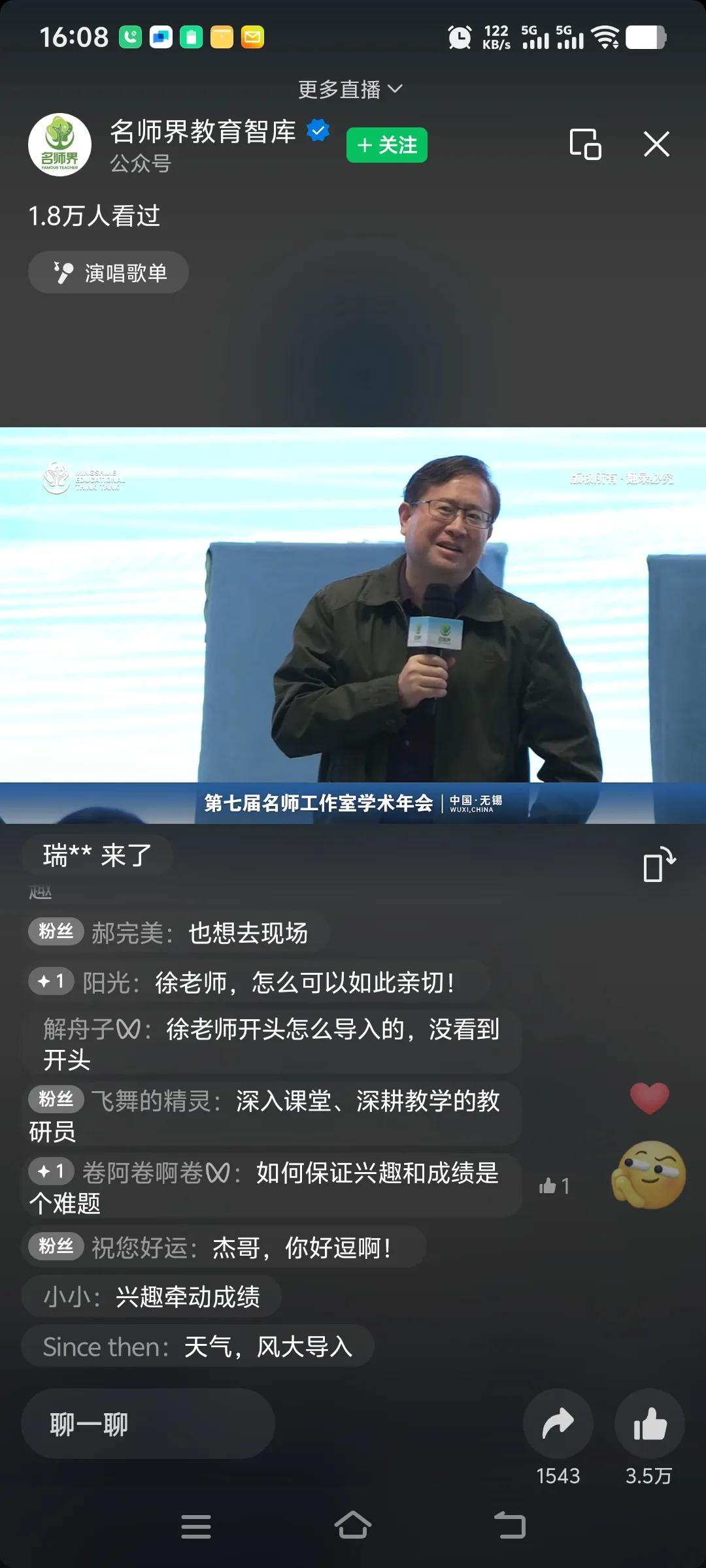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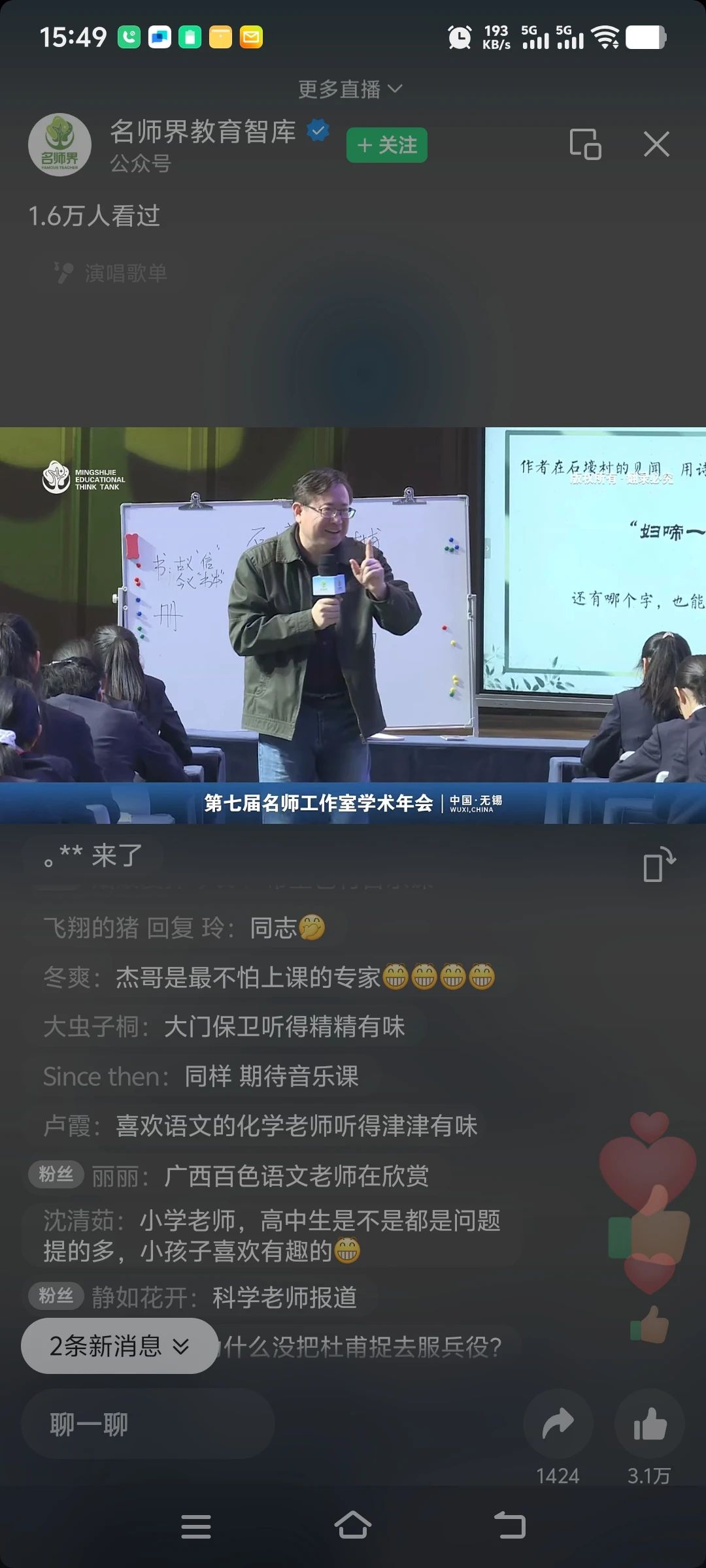




0